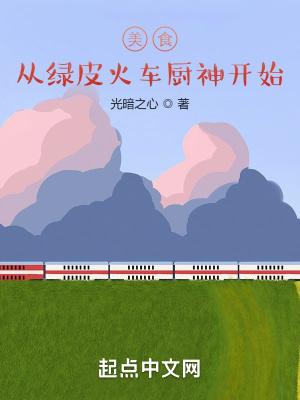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虐文女配的101种be快穿作者 > 44 强取豪夺的女配完 那你这回一定要(第2页)
44 强取豪夺的女配完 那你这回一定要(第2页)
……
养好伤的冯溪又愧疚又难堪,辗转反侧整夜后决定离开东宫,不管是另寻营生也好,去游历四海也好,总归是没有脸继续留在长安了。
他走之前想请王崇州喝酒,被拒绝了还是没有放弃:“就当是还你那次请我的。”
王崇州被他缠得不得不应下。两人再次对饮时,借着醉意,冯溪劝王崇州想开点。
王崇州本就是千杯不醉的体质,嘲讽地看着他发癫。
冯溪见他表情镇定中夹杂着对自己的不耐烦,哼笑一声:“你自以为看得清我的心思,笑话我装模作样,自欺欺人……难道你就与我不同吗?”
听到他这番话,王崇州渐渐握紧拳,手背青筋暴起。
冯溪笑了笑,继续说着:“你比我惨多了,我能看得开,选择离开东宫。但你舍不得离开殿下,哈哈……”
“很好笑?”王崇州慢慢问。
冯溪也有点后悔戳人痛处,抬起头刚要为自己的口不择言道歉,忽然眼眶剧烈一痛。
隔日彩儿送冯溪离开东宫,直到上马车前他都一直低头用袖子挡脸。
她觉得奇怪,歪头细看才发现他为何要如此,惊讶道:“呀!你眼眶怎么青肿成这样!难不成又被人打了?”
冯溪耳朵通红,索性破罐子破摔,放下袖子恨声道:“王崇州打的。”
彩儿意外道:“他打你做什么?”
冯溪冷笑:“因为我戳到了他的痛处。”
“王崇州最是好脾气了。”彩儿嘟囔了一句,明显不信他的话。
冯溪终于品出了王崇州的阴险,当初假装喝醉向他透露辜将军的事,根本就是不怀好意!他抬手摸了摸眼眶,又痛得嘶了一声,转身爬上了马车。
马车落下帘子上了路,听着耳边清脆的马蹄声和滚滚车轮声,他还是没能忍住挑起车帘,向外看着这座富丽堂皇的巍峨东宫。
沿着宫墙马车渐行渐远,他落寞垂眼,终于还是松开了手。
……
女皇在禅位太女之前为郭水姜和夏侯廷赐了婚,从前便已经为二人赐过婚了,只可惜那时候缘分未到,平白错过多年。这一回夏侯廷主动求到了女皇面前,郭水姜也被他的执着打动。
等到二人成婚时,南秀已经登基。
大婚当日女皇和皇夫亲临夏侯府,荣宠可见一斑,其余世家更不敢不给郭家和夏侯家面子,礼单流水一样从早唱到晚。
面对多年未见的齐青长,郭水姜的表弟善韫都不敢认了。若说从前的齐青长尚算温和,如今更多是冷峻,只有面对女皇时才有浅浅的笑意,也许真是从军后磨砺出来的吧,就如同一柄插在鞘中的宝剑,掩藏锋刃却极具威慑。
女皇倒是眼中带笑地望向自己,对齐青长说:“这不是你过去在长安难得的朋友么?”
吓得善韫连酒盏都端不稳了,正慌张地准备起身向女皇陛下见礼,却见她温和地笑笑,示意自己不必动。
齐青长也看向善韫,目露友好,只是仍是不那么热络。
婚宴结束后,南秀和齐青长没有立刻回宫,而是趁夜去了登月楼。
两人坐在登月楼的高台上,远望灯火辉煌的繁华长安。
此刻登高远眺,南秀忽然想起从前来:“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爬到宫里的九层台上看烟火,结果下来后被母皇斥责了一通。”
“不要以为我如今记忆没有完全恢复,就隐去前因后果不提。”齐青长笑道,“可不是因为我带你登高,而是你趁施太傅睡着用火燎了他的宝贝胡子,他带着宫人到处抓你,所以我领你躲在了九层台上。”
他一顿,似乎是在边回忆边说:“结果你不肯下去了,我只好陪你在上面看了大半夜的烟火,第二天施太傅罚你抄的书还是我熬夜替你写完的。”
当时她信誓旦旦说一定会掌灯陪着他,结果趴在他旁边睡得香。
南秀惊喜:“你果然都想起来了!”
之前他还只能回忆起一小部分,如今连细节都能说出来。
笑过后,她语气又有些寂寥:“母皇禅位后没有住在长汤行宫,而是离开了长安……把我一个人丢在宫里了。”
南秀眼底一热,心头有些酸涩。
一场重病过后女皇深感力不从心,有辜时川在女儿身边,她更能放心地离开了。
身旁人轻轻道:“我会永远陪着你。”
南秀笑着侧首看他。齐青长眼中映出她的身影,夜空星河浩瀚,万千光辉也不及他这双眼睛。
她道:“一言为定。”
“一言为定。”
被她全身心依赖着的滋味使他心中柔软至极,抬手轻轻碰她含着薄泪的眼睛,又用指腹轻轻抹掉泪痕。南秀顺势将脸轻轻贴进他掌心,撒娇说:“那你这回一定要长命百岁。”
“我答应你。”他神色郑重,语气认真,令南秀的一颗心终于真正地安定了下来。:,,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