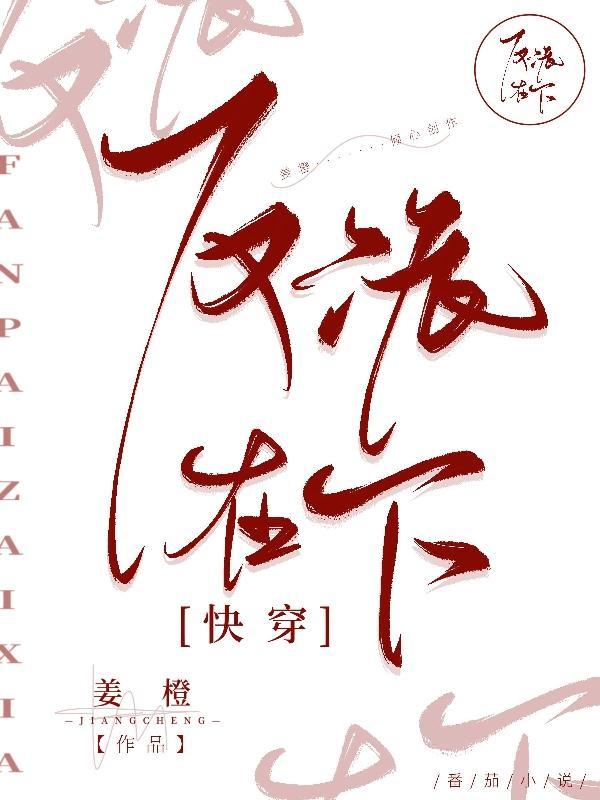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他们是冠军英语 > 第197章 决心和勇气(第1页)
第197章 决心和勇气(第1页)
我就像一名水手,虽然经历了太多的狂风暴雨,但仍然有着寻求新大陆的决心和勇气。——罗伯托·巴乔
说是让他自己加油,隔了两天方蔚然还是联系了当医生的表哥,让他帮忙介绍一个既靠谱,又能远程咨询的心理医生。
“什么情况?”表哥吓了一跳,“出了什么事,你这描述得很像应激性心理障碍。”
“不是我,是我朋友。”
“你在那边还能交到朋友?”表哥也不知想到了什么,口气瞬间严肃,“老实说,是不是同你在黔东南认识的那个男生有关?就是当年你托我帮忙快递东西,又给他找签名足球的那个。”
方蔚然只回了一句:“找医生的事记得保密。”
随后表哥又发了多少痛心疾首的话和表情包,她只当没看见,全神贯注投入工作。
又隔了几天,她带着心理医生的联系方式去找龙峤,却在树生阿公那里扑了个空。
“那小子哪有心思学木工?一天到晚扎在后山挝球哩。”老人摆弄着手中的模型,咔哒一声将榫卯合上,“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挝出啥名堂。”
白天的后山更衣室很安静,只有足球敲击的响声。没有球员的场地上,教练对自己的训练远比对任何人更要疯狂。
方蔚然远远看了一会儿,才在龙峤收球的间隙走上前去。
她知道龙峤的性格,原以为要说服他看诊是个困难的任务,没想到龙峤很爽快就答应下来。
“西班牙的俱乐部也有心理医生,其他国家也有。”他说,“有很多着名不着名的球员都有点毛病,有个和我一起踢球的家伙就冲着自己大腿开过一枪。那时候我很怕俱乐部把我送去和医生聊天,那就说明我真的和他一样了,而且我的西班牙语是真的烂。”
几天不见,龙峤似乎瘦了一圈,但看起来很有精神。聊天的时候,脚边始终盘桓着一颗足球,双眼亮得像藏着火星。
方蔚然静静听他说自己的训练计划和进度:“本来以为要找回状态很难,从前每次想到踢球我就觉得特别难受,腿脚僵硬得迈不开。真的踢起来了,感觉……”
龙峤脚尖一点,球就高高飞起,先落在他头顶,再滑向肩膀、胸膛,又从右腿颠向左腿,全程如被磁铁吸住一般由他任意玩耍。
“我感觉……很神奇。”他说。
双眼盯着方蔚然,有个比喻藏着没敢说出口。
重新踢球的感觉,就像重新遇见她。有痛苦有恐惧,但一旦下定决心不再逃避,一切就变得美好起来。山区经常有这种神奇的事,头顶突然狂风暴雨不要紧,坚持朝前走,走着走着又能变成丽日晴天。
他没有说出口的感受,方蔚然却很明白。
“是不是真的行动起来,就会发现其实没那么难?我做工作也是这样。”她微笑起来,视线追逐着那颗足球,“其实你真的很厉害。不过别再用头球了,你还在吃药呢。”
接下来直到春节,两个人都没有再碰过面。
方蔚然每天忙得脚不沾地,只是隐约听吴彤和杨八一说起,现在龙教练又换了训练方式,果然还是亲自示范来得效率。有时候又听他们笑着议论,原来打职业的照样也会出错,那记长传多么多么漂亮,还不是被我们断了。
写年终工作总结时,她不觉有些失神。春天的时候,她坚决反对的项目,不知不觉竟然成了一年中绕不开的工作。龙峤想送她的“业绩”没能兑现,现在球队却成了她笔下“群众体育强化乡村凝聚力,激活乡村振兴动能”的绝佳案例。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她郑重其事地敲打键盘,为过去的一年总结,也为将来的一年展开希望。
侗家把春节称为“过大年”,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。外出打工人陆续归家,云头寨一日比一日热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