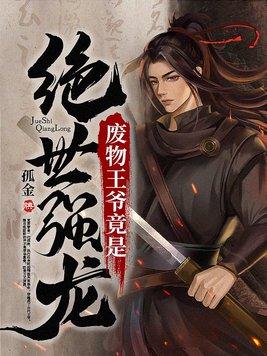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少年特工王 > 第53章 一较高下(第2页)
第53章 一较高下(第2页)
小安对于老头的洗牌熟视无睹,只见他拿起骰子随意地掷了出去,骰子转了几圈之后,竟然是七点,七点是对家拿牌,老头先拿。
老头看着少年掷出了七点,他的心跳加快了许多,他敢肯定,自己这局赢定了。
老头不敢相信胜利来的如此的简单,如此的容易,他没有像先前那样得意地把牌往桌面一拍,而是慢慢地捻开,待到点数完全看清后,老头大吃一惊,奇怪,明明是自己洗的牌,明明是自己亲手抓的牌,怎么会变呢,小的不能再小的一点,仅仅比鳖十大。
再看小安的点数,赫然竟是天对,大的无法再大的天对。
老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他放下牌揉了又揉,再看牌时还是一点。老头的心一下子凉了,他实在没看出来对方怎么出的老千。高手,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
小安看着王东笑眯眯地把筹码划拉到自己跟前。等王东一个不剩地哗啦完,小安捏起骰子掷了出去。骰子滴溜溜转了很长时间,就在众人等得不耐烦之际,骰子突然停了下来,点数还是七点,对门先拿。
老头已经感受不到丝毫的喜悦了,第一把怪异地输掉后,他有片刻的愣怔,他实在想不明白,自己洗的大牌明明是自己拿了,为什么拿到手却是最小的点数。难道这小子会法术?老头为突然冒出的年头吓了一跳,可是眼前的明明是个孩子么,瞧那眉眼,脸上的绒毛都没褪净,不是孩子是什么。是孩子,更是高手,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,活了几近六十,老头没见过。
老头慢慢地捻开牌,竟然是对子,不小的地对。老头又笑了,感觉这局赢定了,除了天对能赢他,地对是碾压一切点子的大牌。只是老头有些奇怪,这地对应该出现在最后一把,它是怎么跑到前边去的,老头困惑极了。
很不幸,老头又输了,因为庄家拿的是天对。
老头面前的筹码已经所剩无几,老头拿眼看向田有利,田有利似乎出红了眼,失去了理智,只见他冲老头大喊道:“我就不信一把不赢,押,全部押下去。”说着,从兜里掏出一张银票,抖了抖说:“昨天赢的就当没赢么,老子有的是钱。”
老头不悦地看着田有利,当着他的面自称老子,老头不气才怪。也许觉得拿了人家的钱财,老头忍了,他一把扯过银票拍在桌上,然后说道:“押五万。”
五万一局,这就是豪赌了,大运自开张以来单局还没有如此大的赌注。
小安笑了,这孤注一掷的赌法说明对方已经失去了理智,而赌博最怕的就是失去理智。要问赌博场上谁最厉害,其实就是敢于离开牌桌的人。无论什么场合,无论输赢多少,只有敢于离开牌桌的人才是厉害的存在,因为那需要极大的理智和定力,君不见许多人之所以能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,全都是因为贪婪,该离开的不离开,赢的还想赢,输的想翻本,就这样一步步沦陷的,直至万劫不复,后悔都来不及。
“看准了。”说着,小安掷出了骰子。
众人屛声敛气,齐齐望着滴溜溜转圈的骰子,心思各异地期盼着他们想要的点数,甚至有人暗暗念叨“七,七,七。
骰子终于停了下来,一个三点,一个四点,加起来正是七点。五自手,七对川,老头先拿。
老头喜形于色,正是他希望的点数,自己洗的牌,正好又是大牌,于是老头伸出的手不由地有些哆嗦了。其实也不怪他哆嗦,行走江湖这么些年,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赌场,也出过各式各样的老千,但是像今日这样一局押这么大的赌注,这还是第一次。第一次虽说不是他出钱,但是也由不得他不兴奋紧张,一掀一瞪眼,不是一瞪眼的事,而是五万大洋,乖乖,这数目任谁都不会等闲视之。
老头慢慢捻开牌,随着点数的显现,他“咦”了一声,他明明记得这是一副天对,咋突然变成了鹅对呢。老头甚是困惑,可鹅对也不小,赢所有杂对和单点。于是,老头把牌往桌上一拍,爆喝道:“鹅对。”
鹅对已经不小,一般情况下会赢,鹅对碰上天地人的情况少之又少,除非点子背到家了。
小安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手中的牌,然后一点点捻开,这动作直把旁边的王冬引诱得焦灼不安。其实也不怨他焦灼不安,毕竟这是赌场开业以来最大的赌局,一局就是五万大洋,要知道一处好的宅院才上万,五万是个什么概念可想而知。这一局赢了,赢的不单是钱,而是他大运赌场的脸面和名声,还有他王冬的未来。
天地人鹅,小安手中的正是人对。
“人对。”旁边观战的王冬大喊道,然后拿过牌使劲拍到牌桌上。
天地人鹅,人对压鹅对,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结局。
老头呆了,田有利也呆了,跟随身后的四个保镖也呆了,原本以为鹅对已经不小了,肯定能赢,结果还是输了。输了也就输了,赌博么,没有和局,只有输赢,问题闹心的是就压那么一点,说得难听点就是强暴。大小点子悬殊过大有人心甘情愿,心平气和,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只压那么一点点,这就难受了,难受了还没法说出来,这才是最难受的,被强暴的滋味不好受。
老头面色惨白,他勉强站起身,对田有利一抱拳道:“老朽尽力了。”
田有利像是傻了,对老头的话充耳不闻,他看着牌一动不动,似乎那牌有着无限的吸引力,或者说把他的魂给勾走了。
小安笑了,这是许多输牌的人的终极反应,不奇怪。
老头看田有利像是魔怔了,也就不再管他,他对小安一拱手道:“有机会我还是要向阁下讨教讨教的。”
小安潇洒地打了个响指道:“随时奉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