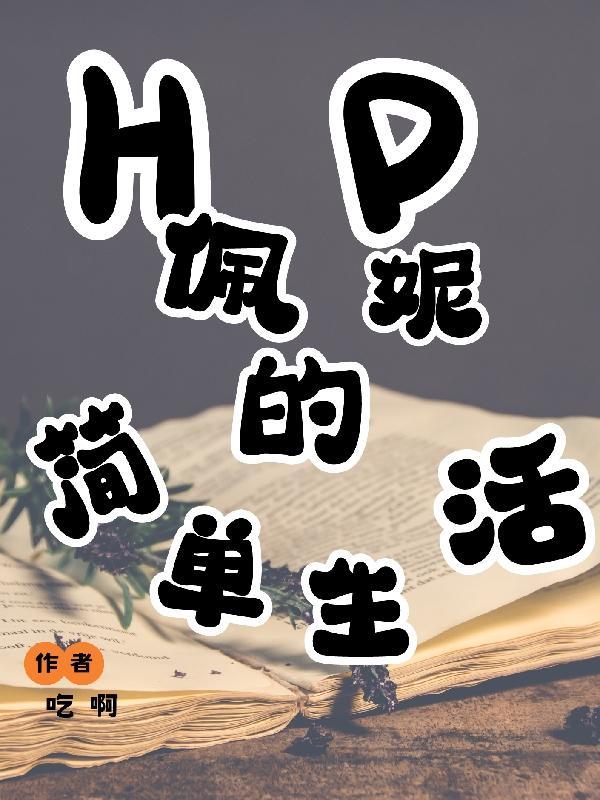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织魂引书评 > 第65章(第1页)
第65章(第1页)
李时胤越发好奇:“哦?到底怎么了?”
老疾医拈须,目露异光,压低了声音,“最近老朽发现,张老三的大腿上被割了许多肉。那伤口整齐,新伤叠着旧伤,似是被刀法熟练的刽子手小心片下来的。老朽多日观察,心中疑惑不解,这好端端的,他为什么被人割了肉?遂让他去报官,他竟然不识好歹叱骂老朽多管闲事。”
“何止是奇怪。”李时胤呷了一口香茗。
老疾医面色悚然,白须都在颤抖,睁大眼道:“后来才发现,那肉是张老三自己割的!”
“缘何如此?”
老疾医平复了心绪,镇定道:“有一日,老朽看诊去早了半个时辰,无意间撞见他府中家丁神色鬼祟地端着托盘,托盘中盛着一支匕首。这本来没什么紧要的,可那匕首上有血迹,张老三正在里间哀嚎。老朽以为是那家丁作恶,以下犯上,要拉着他去见官,连番追问之下,那家丁才战战兢兢说是张老三自己割肉喂了双生子。”
李时胤叹气:“看来张掌柜先前的失血过多之症,也跟这对双生子有关了。”
“小郎君聪慧!”
“那家丁说,起初孩子只是嚷嚷要饮血,这已经够离奇了,然而他们渐渐越长越大,就不满足饮血了。半夜他们总是嚷嚷着太饿,拿着刀让张老三割肉吃,不然就哭闹、殴打家丁牲畜,说自己要活活饿死了。”
“而且,不给他们吃肉,他们确实会肉眼可见地消瘦、短缩下去,像饿痨鬼。可怜见的,张老三一辈子是个铁公鸡,那是妻奴多吃口肉都要吹胡子瞪眼的人,然而这次却心软了。这毕竟是自家的香火呀,又是他身上掉下里的肉,有什么办法呢,只能忍痛每天割两片肉给孩子先吊着他们的命,再找法子医治。”
李时胤补充,“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,毕竟,孩子越长越大,胃口自然也越来越大。长安牲畜遍地,要肉还不简单,可为何他们偏偏要吃他的肉?”
老疾医连连摇头叹气:“张老三哪会不晓得勒?他早就寻遍长安,休说普通牲畜,便是那豹子肉也曾高价猎来,甚至还……”
他声若蚊蚋,“还让府中小厮割肉,还去菜市口的断头台找那死人肉,可那对孪生子真不是一般孩子,竟有神通似的,一眼便瞧出端倪,任张老三如何哄骗一口不吃。”
“那他可有其他什么打算?譬如这对双生子其实很邪异。”
老疾医摆手,“家丁说,张老三的舅母就曾劝告过他,让他不要太过得意忘形,好好思考这对孩子的来路,莫不是什么妖孽。他勃然大怒当场将舅母扫地出门,此后还有谁敢提呢?”
“他活一口气,为了子嗣后代能忍常人所不能忍。而且,那对双生子除去饮血吃肉这一点,倒真是天纵奇才般的人物。”
说到此处,老疾医眼睛亮起来,“出生不过几日,便能识文断字,现在还懂音律、会抚琴呢!若是长大了,那定然能封侯拜相,大有作为。张老三十分自豪,即便身体不适,也到处请人来家中看双生子吟诗作赋,街坊邻居赞不绝口,都艳羡得很呢。”
“那两个孩子嘴甜得哟,哄得张老三团团转。”
老疾医又道:“不过,这样的孩子,常人也确实无福消受。”
李时胤默然。
一个接一个的把诊切脉之后,老疾医捻须下了诊断:“各位都是受了暑热影响,夜咳生痰,鼻流浊涕,此乃肺气不清、暑热犯肺。老朽开一帖药,煎服三日便能好了。”
又闲聊了几句,老疾医便匆匆请辞,要去张老三府上替他换药包扎了。
李时胤将此事告诉了正在饲弄花草的寅月,寅月却没有一丝意外,只头也不回地道:“也不晓得这善果能不能熟。”
“割肉着实是有些残忍了。”李时胤压着袖子轻咳了几声。
寅月幽幽道:“求姻缘求平安求富贵都有代价,何况是强行扭转天命,这点儿代价都不受着,那怎么可能呢。凡人的福德都有记数,用一点儿就少一点儿喽。”
李府众人喝了几日药之后,就渐渐痊愈得七七八八了。
这日天降暴雨,张老三却提前命人递来拜帖,晚些时候,他便携着仆从们来了李府。他已经完全无法行走,只能奄奄一息地躺在软轿中。
风雨如晦,轿夫稍稍走得不稳,都能引来他厉声呼痛、大声斥骂。
随行而来的,除了给张老三撑伞抬轿的家丁,还有两个粉雕玉琢般的年画娃娃。
两个娃娃长得一模一样,约摸七八岁的样子,白嫩大眼,颈子上戴了金项圈。脑袋上都扎了小辫,用丝绦细细地束好垂在脑后。
娃娃们逢人便笑,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,令人一见便十分喜欢。
轿夫们费了好大力气才将张老三搬到花厅,两个娃娃在廊庑下互相追逐嬉戏,吃糕,嗅栀子花。
张老三一见寅月,便虚弱地纵声哭道:“寅娘子,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,才不请自来,请您替我想想办法。”
却见那张老三面色蜡黄,双眼深陷,身上的玄袍宽大得都能淹死他。裤管里空空荡荡,风一吹就能看见凹陷进去的轮廓,连层层的纱布也盖不住。
他两条腿有气无力地耷拉在椅子上,像是两根腐朽的竹竿,柔脆易折。和先前那个高大壮硕的形容不同,他仿佛已经油尽灯枯了。
“不妨事,你请说。”寅月面无表情道。
张老三涕泗横流:“今日冒雨前来,为的仍然是犬子的事情……”
寅月静静看着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