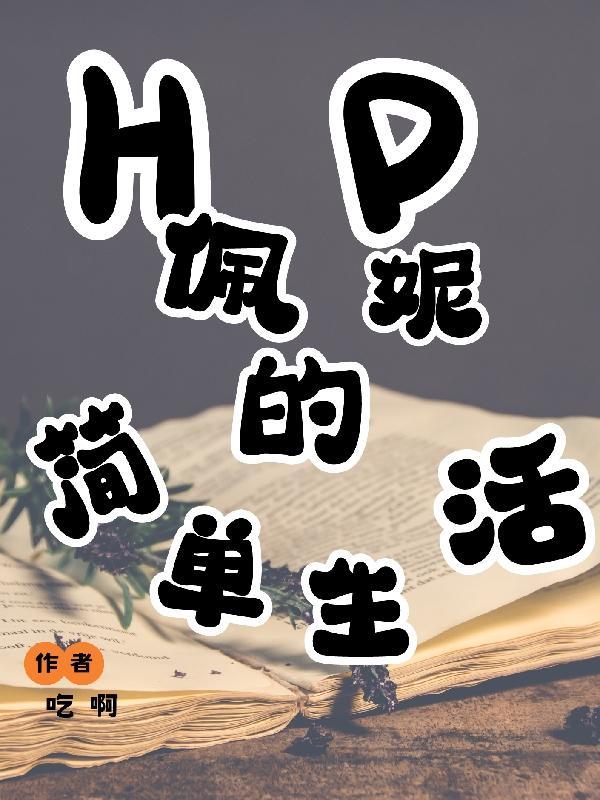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鸡鸣狗吠的拼音怎么读 > 第十八章(第1页)
第十八章(第1页)
青州新送来了些牡丹花株,说是新培育出的品种。
阮鸾筝本来以为它今年不会开花了——注意到的时候却已经开的很好了。
墨紫色的花瓣层层覆覆,重叠翻卷,凑出一个精致美丽的花团来。
阮鸾筝看着喜欢,让人采了花来描。
她的花鸟画师从刘杀鬼,曾经把画混在师父的画轴里给杨子华看。
杨子华与刘杀鬼都是大家,多年老朋友,为人清傲,说话也损。
“天地自然,人心营构……”
他挑剔半天,忽然眼前一亮,从画卷堆里把阮鸾筝的画挑出来,赞了一句,“只这一副,尚还有几分灵气。”
刘杀鬼那时候老叹气,说,“你怎么就不是个男儿郎……”
阮鸾筝对着他一挑眉,心里怎么想姑且不论,但嘴上就要说得不稀罕,“我跟师父学画,是因为兴趣相投,又不是为了承继衣钵。”
阮鸾筝成婚那天,刘杀鬼本早已封笔,市面上一幅画作千金难求,但还是托了人送了一卷新作的百鸟朝凤图来。
后来阮鸾筝做了公主入了朝堂,两人便不再见了——不是不想见,实在是顾忌太多。
有人私底下说,华阳公主府如今这样在朝野中不上不下卡在瓶颈处,错就错在华阳公主不是个男人,薛麟却生成了个儿子。
不过到了现在这个时候,人们往往只道可惜,却没人再可怜他们是什么孤儿寡母了。
阮鸾筝在案上画工笔,薛麟趴在旁边,安安静静地看着她的笔一点一点的动,像是只猫儿一样。
阮鸾筝晕了一遍底色,才放下笔问他。
“说吧,遇上什么事了?”
薛麟半直起身子,看着浑身的不自在,“没什么……我只是想多跟你呆一会儿,你要嫌我我就走了。”
阮鸾筝在手腕上揉开几滴精油,轻轻笑,“你从小就是这样,遇上不好的事就先想着把自己藏起来。这次最起码还愿意跟人说话,倒是多少长进了些。”
薛麟知道自己瞒不过她。
他抓着阮鸾筝的袖子边沿轻晃,下意识地放软声音撒娇,“如果我真的是个女孩子,是不是对我们都更好些?”
他可能不是第一次这么想,但绝对是第一次这么问。
阮鸾筝歪了下头,倒是没有像薛家人一样斥责薛麟胡说八道。
她只是问,“你不喜欢现在的样子吗?”
薛麟摇头,“我只是觉得,好多人都对我是个男孩的事情不满意……”
华阳公主府今年又栽植了些新的花草,高矮错落,在太阳底下显出莹润的翠绿色。府中年年都有新颜色,园设换了又换。
岁岁春色,皆是满目琼花玉树。
阮鸾筝还记得小时候薛麟哭着问她,“他们讨厌我,我做错什么了吗?”
好多人说薛麟没有父亲,家里没有男人,所以华阳公主府立不住门户。
于是阮鸾筝想,那我多放几个男人在府里不就好了。
她养了护卫,加强华阳公主府的防护;收了男宠,甚至在重新遇上姚赫之前便打算再找一个驸马——结果却不怎么好。
她与世界相互厌恶,前人如她一般者寥寥,没有什么经验能让她参考,年岁不算小了也只能在世间被迫懵懂,茕茕孑立,却还执着地寻找一条与世界共存的路。
她抬手碰了碰薛麟的脸颊,“如果不是你自己想要的,不要管别人怎么想。你做你自己就好。”
薛麟在她手指尖蹭了蹭,没说话。
春风已经温暖了,吹在身上又轻又柔,薛麟蜷在阮鸾筝手边,不知不觉就睡到了正午。
阮鸾筝的画画好了,挂在一旁等着晾干,绢布透着光,墨色的牡丹花像是罩着梦中仙境里的雾气,随风飘渺。
阮鸾筝已经净过手,听见动静回过头来,“你醒了,那我们用饭吧。”
薛麟看着她站在阳光里,像一株亭亭的兰草,窈窈窕窕。
——少年心事来得快去得快,现下他又觉得,只要太阳还在,阮鸾筝还在,那其他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他直起身,“阮旸近来身体好一点了,我去叫他一起。”
他想起姚赫也快回来了:阮鸾筝、姚赫、阮旸,还有他,四个人凑在一起,感觉像是一家人一样。
阮鸾筝在身后唤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