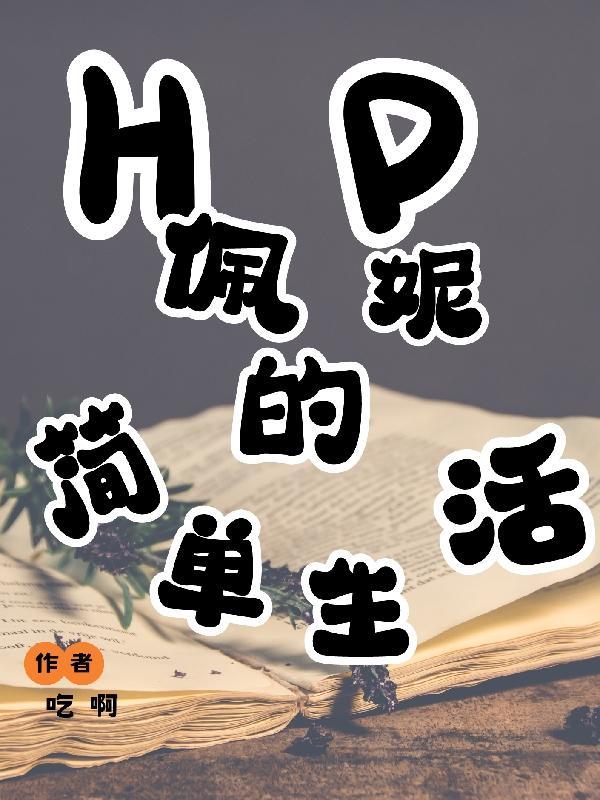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鸡鸣狗吠的拼音怎么读 > 第十八章(第2页)
第十八章(第2页)
“不要这样急躁,当心……”
话还未说完,薛麟已经跟人撞了满怀。
这人好像根本没打算扶他,是薛麟自己抓着他胳膊站稳的。
薛麟的鼻子撞得有点疼,仰起头看这个人,眼睛里满是困惑,“你是谁?”
这人板着一张棺材脸——全身上下都板着,皮笑肉不笑的,“在下是魏王府的侍卫”。
薛麟摇摇头,“我没有见过你。”
“区区一直在魏王手下。郡王若不记得,想是贵人多忘。”
这人说话不好听,好像带着刺,透着些古怪……
薛麟眉头一皱,想先把人抓起来再说,却听身后阮鸾筝说,“麟儿,我认得他,带他过来。”
阮鸾筝将这人上下打量过,嫌弃地像是看见一株长大后变得不合心意的流苏树。
“你来做什么?”
这人向薛麟那边示意了一下。
阮鸾筝不为所动,“你说吧。”
他顿了一下,看华阳公主打定了主意不让步,也不再跟她僵持。
“少主今天出门时,遇上了高阳王的小王子,有了些争执。”
薛麟眼一睁,“许知意?他什么毛病!阮旸跟他能有什么争执?”
这人还是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,“王子说,少主叫人把他套麻袋打了。”
薛麟一时没反应过来,“……啊?”
薛麟坐不住了,饭都没动要跑去找阮旸,找之前先看着阮鸾筝。
阮鸾筝向他挥挥手,他便放心地跑出去了。
他一走,画廊里就只剩下阮鸾筝和这人面对面。
“说吧,”华阳公主坐下,“你把麟儿特地支走,到底是有什么事?”
这人打趣说,“殿下一点不担心吗?”
“孤是该担心阿旸?还是高阳王?”
——在她眼里许知意不过是逞父兄的荫蔽狐假虎威,根本入不了眼。
“高阳王此人色厉内荏,好利喜功,贯会见风使舵。就算阿旸不小心把他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打死,只要面子给到了,他也不会说什么。”
这人站在她对面,也不知道这话哪里触动到了他,面色略微和缓下来,“殿下看不起他?”
“孤看不起的人多了。”华阳公主冷哼一声,“逄宪,我看在二哥的面子上跟你啰嗦了这么半天,你别不识好歹。”
逄宪是阮玄沧当初从人贩子手里买下的“菜人”。
他小时候瘦的厉害,真整个炖了也熬不出几碗汤来——皮骨全都单薄,但是人很固执,追在阮玄沧的军队后面,像是溺水的人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你怎么劝他吓唬他都不肯放开。
阮玄沧后来松了口,收了他当徒弟。一转眼也长这么大了。
逄宪跟着阮玄沧长大,见了阮鸾筝说话也还算客气,开口先跟她谈天谈地谈工笔画。
“殿下知道这花叫什么吗?”
阮鸾筝瞥了桌上的牡丹一眼,又看他,没说话。
逄宪接着说,“是‘青龙卧墨池’。主公当时觉得名字有趣,特意叫人在朔川南部养了一批幼苗,说是等养好了叫齐王一起看新鲜。等到花开的时候又后悔,说他们两个俗人看这花纯粹是在糟蹋东西,应该叫上殿下一起,您一定会喜欢……后来几经辗转,成株最后还是送到了殿下府上。”
他说的事阮鸾筝有一点印象,当时她以为阮青崖在跟她炫耀,生气的不行。
她指尖点在桌上牡丹花花瓣上,轻轻叹了口气——墨紫色的花瓣层层叠叠,其正中的雌蕊成青绿色,恰似青龙盘卧于墨池中央。
“二哥总觉得,我跟四哥能像他跟我,他跟四哥一样的相处。虽是好心,但做这许多,也只是徒增尴尬而已。”
“为什么?”逄宪好奇。“齐王得罪过殿下?”
“那可多了。”阮鸾筝回答的毫不犹豫。“论打数论车装,我能连着跟你说上三天。”
逄宪一直板着的脸上竟然带了点笑意,“殿下可愿与我说两件听听?”
阮鸾筝神色带了些无奈,“你们这帮孩子,怎么都这么八卦呢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