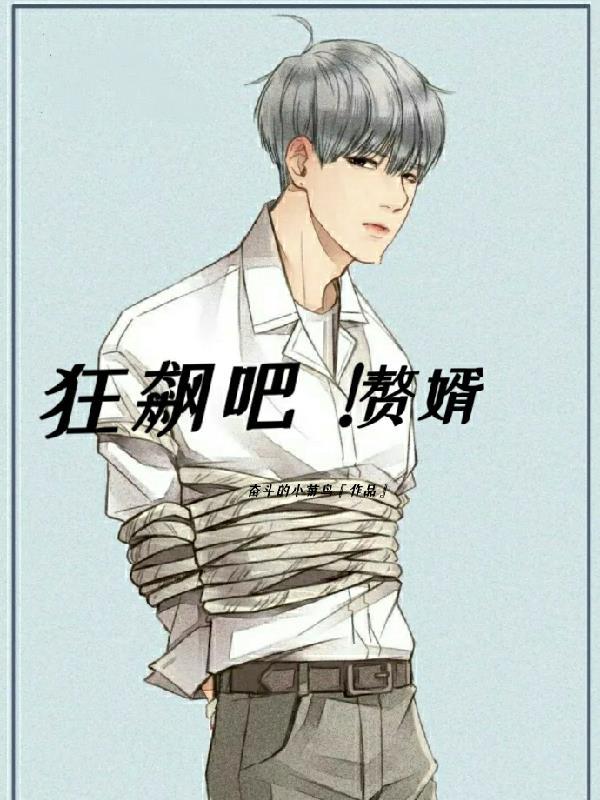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自甘上流讲什么 > 第74节(第1页)
第74节(第1页)
“那最艺高人胆大的是你,现在还不走。”杜秋靠在他腿上,懒洋洋打着盹。男人的腿枕起来没意思,硬邦邦的,可她也懒得动。到这时候她还是信命中注定的,自己也没想到会怀孕。可是一切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帮着她,留住他。
或许有人会说靠孩子挽救的婚姻没意义。无所谓,由他们去说吧。
叶春彦这样的人,能为她放弃原则,就是她权力王冠上的最大的一枚宝石。她到底还是赢了。
杜秋怀孕的事,叶春彦只和最亲近的朋友说。关昕上门来贺喜,因他是独自一人来的,杜秋便随口问了一句关太太。
关昕支支吾吾解释。原来关太太正卧床休息,他们楼底下一户人家装修,断断续续快一年,闹得关太太休息不好,找了物业投诉无果,上门理论吵了起来,关太太气到胸口疼。
杜秋道:“你们住哪个小区?哪家物业?我直接给他们老总打电话。”
关昕看了一眼叶春彦,面有难色。杜秋以为他不满意,便道:“再不行报警,我找人帮你处理。”
关昕摇摇头,道:“谢谢杜小姐的好意,只是我们小老百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不想让事情搞太僵。以后都是邻居,我们想再去谈谈。沟通一下。”
杜秋怔了怔,面上略有不可思议的笑,好像从未想过有这样的出路。她的世界里只剩征服与顺从,试探与欺骗,对沟通一词,生出些好奇。
关昕要走时,叶春彦特意送他到车库。上车前,关昕转身,颇为郑重地握了握他的手,道:“你看着挺辛苦的,一定要保重身体。”这话像是他踌躇了很久才说出口的,再深一些说,就要担上挑拨的罪名了。他也不过是担心罢了。
叶春彦笑道:“我明白的,没有事的。你多照顾好自己。”
等关昕走后,杜秋抱怨道:“都这样了还沟通什么啊?要不要私底下给他们解决了?”
叶春彦立刻劝下她,道:“别,他们选了一条和你不同的路。”
“如果是你,你会怎么做?”
“我基本不和人吵架。因为大部分人不是瞎子。关太太只有一米六,还那么瘦,吵架自然没人怕她。可是我这样的人,想讲道理的时候,多数人还是会听我讲道理。”
杜秋欲言又止,叶春彦则又想起来母亲和自己艰苦的痛苦,道:“这个世界欺软怕硬,踩低捧高,要想无权无势活着,是要一点运气和手段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,我和你对世界的看法是一样的,甚至更悲观。但我依旧不能认同你。”
而出乎他们意料,关昕竟然靠沟通顺利解决了此事。邻居听说关太太病倒了,亲自带着水果,登门道歉。两边各自退让一步,事情倒也过去了。
叶春彦自嘲道:“看来倒是我们太小心眼了。”
由此他忽然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。母亲活着的时候,也和邻居吵过架,那时候还是高一。他正在窜个子。有人总爱把自行车搬到楼道里,入夜后上楼不方便,刮蹭到他好几次。母亲心疼他,上门和邻居理论。
等他放学回来的时候,他们已经吵起来了。邻居是一对父子。儿子理直气壮地骂着人。母亲脸皮薄,根本就落在下风,连看热闹的人也不偏帮她。她急了,叫嚷起来都破音了。
邻居对着叶春彦道:“你妈疯了,多看着她一点。”说话时用的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。自有他的道理。毕竟在这世上,女人不过是这几类。疯子,婊子,妻子。
他不说话,只是护着母亲回家去了。门一关,母亲就趴在桌上哭了,“我想让你过得好一点。是妈妈没有用。”他记忆中母亲是个很少流泪的人。
叶春彦尴尬地走开,没说话。找了一个休息天,跟着邻居出去,就着他的脸给了两拳,从口袋里掏出水果刀,道:“小心点,我还没成年,宰了你都不犯法,有种试试看。”
还有热闹时最得意的一个人,他也默默记下了长相。等天黑后,他捡起一块石头砸碎他家窗户。趁着他骂骂咧咧下来看,叶春彦立刻从隐蔽处出来,抓着砖头砸向他后脑勺。第一下就把人打懵了,他立刻把塑料袋套上去,不让对方回头,踩在背上连踢几脚。
逃回去的路上,他撞见了一个老太太,是以前的街坊。她见到他凶神恶煞,衣襟上带血也吃了一惊。
他第一反应是威胁。抓着手上的砖头,往地上一丢,恶狠狠道:“你敢说出去,一个人的时候就小心点。”
“你这孩子,怎么变成这样了?”
叶春彦愣了一下,落荒而逃。这件事没有后续,除了邻居不久后搬走了。之后暴力就是他的朋友,直到割下了别人一只耳朵,他也没有特别的愧疚。
看着他们满脸血求饶,他只默默地想。真可怜,刚才还一脸嚣张,现在却像条狗。他百无聊赖地把一个烟头踢到他们脸上。回头望着高挂的遗像。
妈妈看到这样的他,究竟是难过还是骄傲呢?
转变还是在汤君出生后。为了一件小事,汤雯和人有争端,那时候她还在哺乳期,气得差点喘不过气来。他揪着对方的领子就往外拖。汤雯劝他算了。孩子哭了。
奇怪的是,他放过对方后,汤君不用人抱,就停下了哭声,自顾自笑起来。从那天之后,他就发誓洗心革面,不再让暴力的轮回,伤害到孩子。
像关昕一样普普通通的沟通,普普通通的谅解。他和杜秋都无从想象。他们从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个世界。
屈辱,伤害,不甘,怨恨。这是他们共同的起点。恰因为是镜中相反的倒影,所以他们才在某一刻如此相似。
他是真的悔改了吗?还是说,他的沉默与宽恕本就是一种更深的倨傲。
十月是叶春彦的生日,可是生日会请来的全是汤君的同学。她还在振振有辞道:“没办法啊,爸爸没什么朋友的。”
除了几个相熟的朋友外,还叫来了学校戏剧社的社长。叶春彦还以为汤君和他关系一般,不过孩子间的友谊总是很奇妙的。这个小社长长得团头团脑,像是个糯米团子里嵌着两颗桂圆,不过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,也不和其他人玩。
叶春彦怕他和女儿闹别扭,偷偷跟着,却意外听到汤君和他躲在阳台说话。原来下学期他就要转学了,他父母离婚了,双方都想带走他。他犹豫不定,选谁都像是太自私了。
汤君道:“别烦了,你选谁都一样的。大人离婚后很快会有自己的生活,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小孩。你选一个对你好的就可以了。”
“你把大人们说的好坏啊。”
“没有啊。人就是这样的。没人可以永远幸福,所有人幸福就是所有人不幸福。能让自己开心就很了不起了。我就要一直开开心心。别想了,快去吃蛋糕吧,然后我们去打游戏。”两个孩子手拉手,快快活活走了。
叶春彦留在房里,反倒陷入沉思。他的童年,杜秋的童年,汤君的未来。有申辩的路,有反抗的路,有顺从的路。众人各走在众人的路上。
因为都是孩子,花钱请了一组人来表演魔术。纸牌变花硬币一类的小把戏。汤君之前看过彩排,有些嫌无聊。叶春彦拉她到一边,语重心长道:“这个世界上很残酷。我小时候就这样,现在也一样。我总是想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给你,不想给你坏的影响。现在想来我可能错了。因为我和你看的世界,原本就是不同的。我以为对你好的事情,可能并不是这样。”
汤君模模糊糊笑了一下,不是太懂,也有些不耐烦。她再怎么装成熟,也还没到理解这话的年纪。“爸,你要吃蛋糕吗?有巧克力夹心的好吃。”
她蹦蹦跳跳去给他拿蛋糕。叶春彦有些好笑地想着,这个家里的女人怎么每个都这么不客气。今天到底是谁的生日啊?
吃着蛋糕,叶春彦看汤君招呼小社长玩打游戏,问道:“你怎么把他请来了?我还以为校庆上他让你演配角,弄得你不高兴。”
“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和他不好,所以我要把他请过来。这样同学就都觉得我人很好。反正他要走了,等下学期我去竞选了戏剧社社长,大家支持我,我就要当主角。”
该说这是缘分吗?她已经越长越像杜秋了,又不全是耳濡目染。叶春彦开玩笑道:“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。”
“切。我才不喜欢爱哭鬼呢?”
“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啊?像我这样的?”叶春彦不由得意起来,到底女儿是和他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