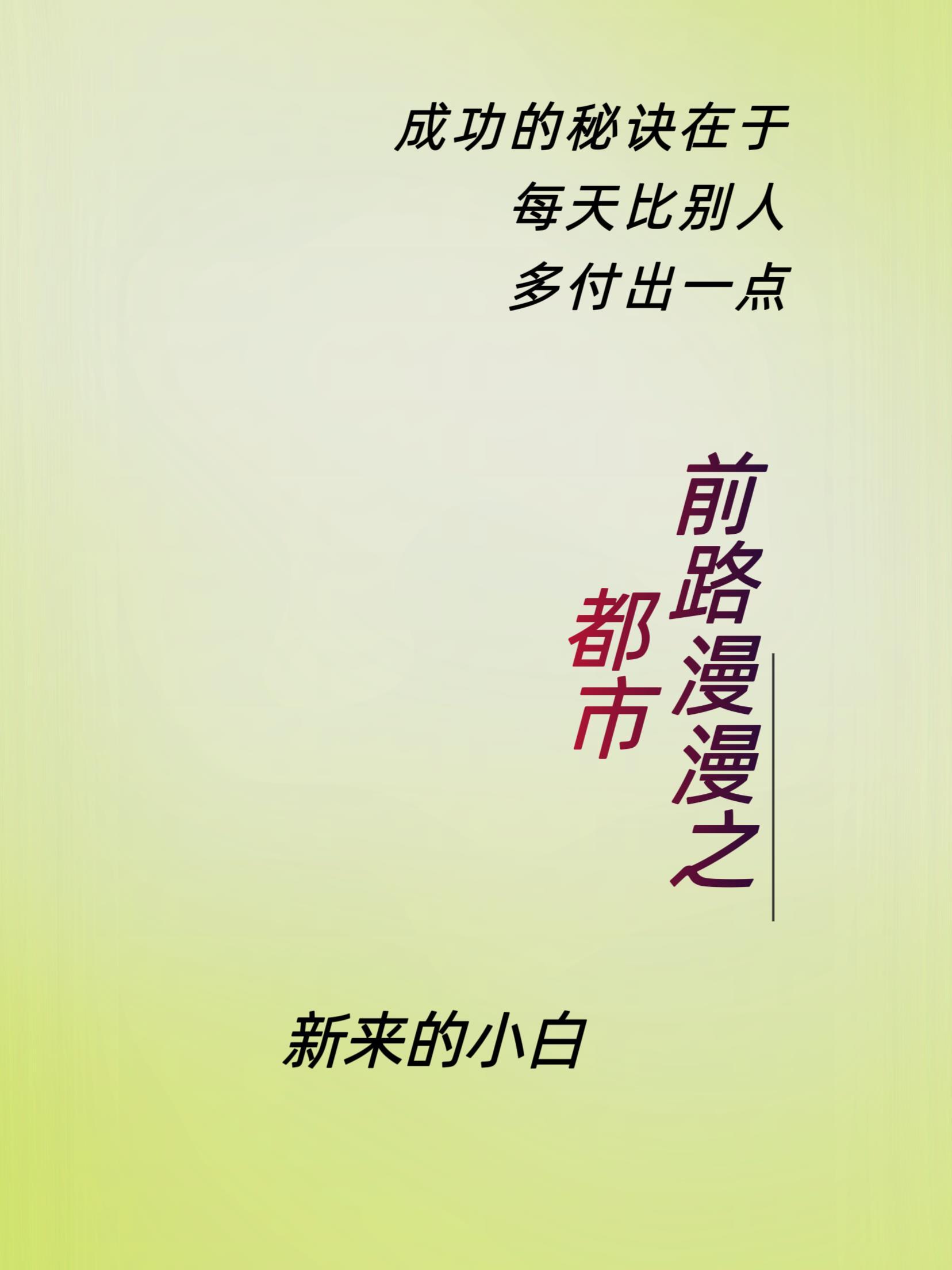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穿成寡夫郎之后114章全文免费阅读 > 第552頁(第1页)
第552頁(第1页)
秦子文都以為他醒不過來,就這麼永遠地睡下去了,沒想到秦仲居然醒來,一看到他,眉頭就皺緊:「怎麼……是……」
後面的字,怎麼都說不出來。
秦子文十分有孝心地把被子給他掖一掖:「父皇是說,怎麼是兒臣在此,不是其他皇兄皇弟在這兒伺候您?」
「他們都在外邊呢,還有文武大臣也來了,全等著父皇醒來。」
秦仲不想見秦子文,他,他的母妃,以及衛家,是秦仲心頭的一根刺,秦仲壓根不相信秦子文會希望自己好好的。
他也不信宣親王賢親王等人,現在,他唯一信的,只有從離州趕來救駕的顧凜。
他歪靠在枕頭上,看向內監:「叫……顧……凜進來,朕有……話……」
內監點頭,明白了他的意思,彎著腰對秦子文道:「王爺,您先出去稍候,待皇上與顧大人說完話,您再進來照顧。」
秦子文起身,拍了拍衣袍走出去。
殿門外的文武大臣少了半數,少了的要麼是忠於秦仲這個皇帝的,要麼是幾個親王的互相的陣營的,剩下的多是騎牆派,誰登上帝位他們擁護誰。
只是沒想到秦子文這個隱形王爺會站在這兒,望著他有種恍惚之感。
秦子文的目光在他們身上一掃而過,走到顧凜跟前:「顧大人,皇上叫你進去,有話跟你說。」
「是。」顧凜頷,抬腳走進寢殿。
看到他來,秦仲臉上總算有幾分鬆快,在他眼裡,顧凜是真正忠於自己的人,自己現在病情有些嚴重,為了防止圍宮之事再次發生,讓顧凜時時刻刻守在他身邊是最重要的。
等他病情好轉,一定要把那幾個逆子碎屍萬段!
他渾濁的眼睛望著顧凜,歪斜的嘴顫抖著,道:「愛……愛卿……恆王狼子野……心……,不可……留……」
「尋個由頭……將其扣押……」
內監眼觀鼻,鼻觀心地站在龍床邊上,猶如泥塑木雕。
顧凜望著秦仲,目光一如既往地冷然,他不喜歡浪費自己時間的人或物,眼前的秦仲已在此列。
若非秦仲昏聵,朝廷如一團爛泥,自己現今該與林叔一道在離州,而非坐在此聽一個連話都說不清楚,上下失禁的人說話。
顧凜開口,道:「陳大伴,取皇絹和筆墨來。」
陳大伴身體一抖,望著手握重兵,解了京都之危的顧大人,終究悶著頭去取只有皇上書寫聖喻才能使用的皇絹以及紙筆,擺放在桌案上。
秦仲目眥欲裂,他望著忠於自己的顧凜,「你……你……要……」
顧凜眉尖蹙了蹙,一手抓著被秦子文掖得整整齊齊的被子,按在秦仲的臉上。
被子微弱地動了動,本就半癱了的秦仲被捂住口鼻,沒兩下就停止了動彈。
顧凜鬆開手,對面無人色的內監道:「給皇上整理。」
陳大伴撲通一聲跪在地上,身體抖得像篩糠:「是……」
他連滾帶爬地到龍床前,顫抖著手把秦仲瞪大的眼睛合上,將捂在他臉上的被子拉下來,仔細地掖好。
而顧凜走到桌案後,撩著袍子坐下來,磨了磨墨後拿起刻著龍紋的筆,在皇絹上寫下第一個字。
寫完後,他伸手拿過雕刻著九龍的玉璽,蓋在皇絹上。
第319章
輕飄飄的皇絹,墨跡很快便幹了,留下幾行字。
顧凜拿著皇絹起身,對陳內監道:「你是個聰明人,該知道如何做。」
陳內監連連點頭,突然起身往外跑去:「皇上殯天了!」
守在殿門外的文武大臣和眾位因為不能與三位親王抗衡,反而躲過一劫的皇子們聽到這猶如炸雷一般的消息,下意識跪在地上。
而隨著陳內監叫人傳話到各宮,乃至京都內,後宮的妃嬪們不管真情還是假意都捂臉哭泣,京中百姓都對著皇宮的方向跪拜,再急匆匆地去鋪子裡買白色麻布,門口的對聯也要用紙糊上,燈籠亦要取下來。
但相比於這些百姓,處於風暴中心的朝臣和皇子們更明白秦仲的駕崩意味著什麼,一個個心裡都打著自己的算盤。
朝臣和眾皇子正要走進殿內,陳內監退身到一旁,道:「皇上臨終之時吩咐,由顧大人執筆書寫聖喻。」
他說著,顧凜手捧皇絹走到殿門處,展開皇絹。
不管下邊的朝臣皇子們心懷何種心思,都懾於顧凜手中的兵馬,跪在地上。
顧凜目光落在皇絹上,念道:「詔曰:朕登大寶三十七載,勤懇親政,日夜無懈怠,今感大限將至,遂留下此聖喻。」
「皇十一子子文聰慧仁厚,天性純然,宣即皇帝位。皇四子皇六子皇七子謀逆之罪不可赦,奪其親王之位,斬立決,與其犯事主謀者,斬立決,禍不及親族。」
「昭喻天下!」
下面跪著的不少人在聽到賢親王榮親王和宣親王竟然被判了斬立決,脊背發涼。
那可是屹立多年的幾位親王啊,竟然落得個身異處的下場,誰敢相信。
當即就有人含糊其辭地質疑這份聖喻的真偽,說恆王秦子文歷來不得帝心,皇上怎麼會突然傳位給他。
且皇上怎會駕崩得如此快,當場除了顧凜,其他人都不在,保不齊……
話沒有明說,但意思到了。
拿著皇絹的顧凜看了那個官員一眼,走到跪在地上的秦子文跟前,明擺著站在恆王秦子文那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