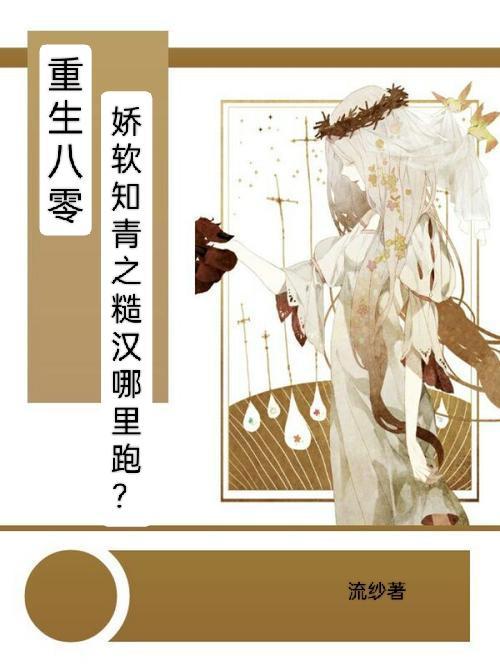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我靠狗血创飞古人 > 第143章 第二册(第1页)
第143章 第二册(第1页)
段娘子出了城,走过平坦的大路,雨后略有点泥泞的乡下小路,回到家里。
放下担子靠在墙边,从缸里舀出去几瓢水,将手脚洗净,用帕子擦干,才提起放在竹筐里装着书的包袱。
她来到了自己开辟的书房,在正房的旁边,是一间不小的屋子。
推开门,里面的四面墙,其中三面是整整齐齐的书架,上面的书满满当当,有纸质书,也有竹简。
有的已经破损不堪,书页将掉不掉,被人用针线将书脊重新缝了起来;有的整洁如新,翻阅的痕迹却明显,显然主人家已经将这些书全都看过,且非常爱惜。
书柜的下方是几个大箱子,里面都放着书。
很难想象,乡间竟有这么一所“陋室”,不知情的人闯进来,怕会以为是哪个书香世家的藏书房。
段娘子收拾一番,腾出点空地来,把新买的几本书放上去,又拿起她一眼注意到的那本书,坐到了唯一一面空余的墙边放置的书案前。
她手指轻轻摩挲着上面的几个字,看了好一会儿,才翻开书,认真专注地阅读起来,沉浸于故事中。
……
看到族人争抢家产时,她蹙起眉头,眉宇间隐现怒色。
见顾母在受到逼迫时指天誓自己绝不改嫁,段娘子露出一个嘲讽的冷笑。
这样没用,心怀不轨者找来的借口,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放过。
她被逼着改嫁时也曾誓过,却无人相信,也不愿相信。
世间的事向来由不得人,女子尤甚,随波逐流,从一个人家到另一个人家,像可以随意买卖的家畜,被主人驱赶着完成从生下来就被赋予的使命。
她整整改嫁了两次,有过三任丈夫,如今孤身一人,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她过得凄惨,无家无室,无依无靠,重活只能自己干,受人欺负没人撑腰,死在屋里也无人收尸。
可自从嫁人以后,这是她前所未有的,过得最轻松的几年,她可以支配自己的所有,无论是痛苦,还是喜悦。
这间屋子,包括里面的书,是她一点点积累起来的,连同她的渴望,她的心也一并填满。
但满足只是短暂的,书看完后紧随而来的是更大的空洞和不满,于是她只能不断地去找书,去看。
不光看,她还会自己做记录,随意地写些东西,积攒出来的纸稿,整整堆满了一个箱子。
书让她挣扎出现时的泥淖,短暂地拥有片刻温存,看向目光触不到的远方。
如同眼前的话本,将她拉扯进别人的人生,参与和围观她们的经历,情绪随之起伏波动。
看完后,段娘子深深地吐出口气,放下书,腰身微弯伏在案上,将脑袋埋进臂弯里。
过了一会儿,抬起头来,面上的表情似喜似怒,放在案上的手,五指蜷缩握紧,指节泛白。
她应该感到庆幸吗?
看到这样一本女子扮作男装,为自己逆天改命的“浊世巨作”,她甚至不像木兰一样是为了父亲。
但无名的怒火烧上心头,灼痛着通向她的四肢百骸。
从故事中抽离出来的那一瞬间,她明白了作者的意图——想让那些浑浑噩噩,一无所知的女子清醒过来。
可她凭什么?天下女儿何其多,她凭什么自以为是特殊的那个,有资格去叫醒别人?
又有什么用呢?清醒过后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痛苦,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作出改变。
她拿出纸笔,笔走龙蛇,在纸上快地飞舞,留下成串的墨迹。
一气呵成写出一封信,她折叠几下装在信封里,之后寄了出去。
。
“新一册了,快看看写了什么。”手里捧着书的人,迫不及待地翻开。
“老天保佑,一定不能让我女儿退学,这可是她千辛万苦求来的机会,否则我穿进书里找那些夫子算账!”
“你入戏真是越来越深,连女儿都叫上了,你看人家认不认识你这个父亲?”
“我单方面认了。”那人拍着胸脯,厚脸皮地说。
“别吵吵了,快看女儿——不是,女主怎么办。”
[
夫子已经注意到了,顾青当然不可能直接销毁罪证,那看上去简直像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监考的夫子拿起纸条,上面写的果然有关于考试内容。
他怒斥她道德败坏,让她滚出考场,并且会取消她的成绩。
顾青试图解释,那纸条并不是她的,是舞弊的人没扔准,她只是受了无妄之灾。
然而夫子找出扔纸条的那个人,问他这纸条是不是扔给顾青的,那人低着头不言不语,看上去像是默认了一样。
尤其这个人跟顾青一样也是平民出身,只比她略微好点儿,很容易让人怀疑是抱团取暖,相互勾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