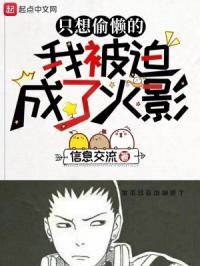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圣殿春秋和世纪三部曲的区别 > 第二十七章(第5页)
第二十七章(第5页)
罗洛才看了一分钟,就嫌内容粗
俗不堪。观众捧腹大笑的时候,他发觉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妇人怔怔望着自己,似乎看他面熟。
他没见过这个妇人,也想不出她会是什么人,但瞧她双眉紧锁,就觉得心中不安,于是掀起斗篷风帽,转身出了庭院。
走到集市广场,他抬头望着主教座堂西墙,恨恨地想,我本该当上主教的。
他踱进教堂,心中失落。新教徒把这里弄得枯燥黯淡,石龛中的圣徒和天使像被砍掉了脑袋,以防偶像崇拜。透过墙上薄薄的白漆,依稀看得出从前的壁画。奇怪的是,美轮美奂的彩绘窗却完好无损,或者因为换玻璃太破费。可惜正是冬日午后,彩绘的色彩不算上佳。
罗洛暗想,我本有机会改变这一切。我会给百姓带来色彩、华服、珠宝,才不是这种冷冰冰、没有一丝人情味的清教东西。想到失去的机会,他胃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。
教堂里空无一人,想必牧师都去看戏了。他转过身,看见中殿尽头站着一个妇人,正是之前那个盯着他瞧的人,竟然跟到教堂里来了。两人四目相对,妇人开口了,声音在拱顶下回响,宛如末日审判。她说的是法语:“C’estbientoi——JeanLanglais?果然是你——让·英吉利?”
他急忙转身,飞快思考对策。现在命悬一线。对方认出他是英吉利了。看样子她不认得罗洛·菲茨杰
拉德,但也用不了多久,她随时可以跟认得罗洛的人指认他就是英吉利,譬如内德·威拉德——那他只有死路一条。
得甩开她。
他匆匆穿过南面侧廊。墙上有一扇门,进去就是回廊。他一扳把手,才发现打不开,随即想到,四方院子让阿福·威拉德改成了集市,门自然是堵死了。
他听见轻盈的脚步声,知道那妇人沿着中殿跑过来。看样子她想凑近了打量自己,好确定没有认错人。不能让她得逞。
他沿着侧廊,匆忙走到交叉甬道,四下张望,寻找出路;得在她看清自己的样貌前混进人群。南侧耳堂墙上开了一扇小门,通往高塔。他担心门后又连着新集市,推开门一看,只有一座窄窄的螺旋楼梯。他当机立断,迈到门后,带上门,沿着台阶上楼。
他一路张望,盼着有门通向正南面侧廊上方的长廊,爬着爬着才发现这天不走运。他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,只能接着往上爬。
爬了一阵,他开始气喘。他五十三岁了,爬台阶比从前吃力。不过话说回来,后面那个紧追不舍的妇人并没有比自己年轻多少。
她是什么人?又怎么会认得自己?
显然是法国人。她对自己直呼“toi”,而没有用“vous”,要么因为她对自己十分熟悉——但情况并非如此,那只能说明她以为自己不配用敬称“您”来称呼。她一定是见过自己,要么在巴黎,要
么在杜埃。
既然是法国人,又住在王桥,那十有八九是胡格诺教徒。倒是有一家姓福尔内龙的,不过老家在里尔市,而罗洛从来没去过里尔。
对了,内德·威拉德娶的是法国太太。
那么身后那个气喘吁吁、紧追不舍的,就该是她了。罗洛想起来了,她叫西尔维。
他时刻希望下一个转弯处连着拱道,巨大的石雕下也许藏着许多条走廊。螺旋楼梯没有尽头似的,宛如一场噩梦。
总算走到台阶尽头,他气喘吁吁、筋疲力尽。面前是一扇低矮的木门,罗洛一把推开,寒风扑面。他弯着腰从过梁下钻过,劲风之下,门砰地关上了。他发觉自己站在交叉甬道位置的中央塔楼,脚下是石头铺的走道,自己和几百英尺下的地面只隔着一道墙,高度不及膝盖。他低头查看,下面正对着唱经班的屋顶,左边是墓园,右边是旧回廊围成的四方院子,改成室内市场后也盖了屋顶。背面的集市被宽大的尖塔挡住了,看不见。风猛烈地掀动他的斗篷。
走道环绕尖塔一周,塔尖上矗立着那座巨大的天使石像;从地面上看,却和真人一般大小。罗洛快步沿着走道查看,寻找另一处楼梯,梯子,或是什么台阶。他绕了半圈,俯视脚下的集市。都去“贝尔”看戏了,集市里没几个人。
他没找到别的出口。他绕了一圈,看到那妇人从门洞里走出来。
狂风呼啸,她
被头发遮住了眼睛。她撩开头发,直视着他。“是你,你就是我在皮埃尔·奥芒德家门口看见的司铎。我得确定没认错。”
“你是威拉德夫人?”
“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找让·英吉利。你来王桥做什么?”
他猜得不错,妇人不知道他是罗洛·菲茨杰拉德。两个人在英格兰从没有见过面。
直到今天。现在秘密被她发现了,他会被逮捕、受严刑拷打,最后以叛国罪绞死。
他随即想到,还有一个简单的出路。
罗洛向她逼近:“你这傻瓜,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危险?”
“我不怕你。”她说着就朝他扑过来。
罗洛死死抓住她双臂,她尖叫着奋力挣扎。罗洛生得高大,但她也不好对付,又扭又踢,最终抽出一只手,朝他脸上抓来。罗洛躲开了。
罗洛把她推到角落,背贴着矮墙,但扭打之下,不知怎么被她绕到身后,最后是他自己背对着地面。她使出全身力气,猛力一推,好在他力气大,又把她按在墙边。她尖声喊救命,但声音被风声吹散,谁也听不见。他用力一扯,叫她向一侧歪倒,紧接着绕到另一侧,眼看要把她推下去了,不料她双腿一软,瘫倒在地上,随即挣脱了,手脚并用地爬了两步,站起身,拔腿就跑。
罗洛忙追过去,沿着走道狂奔,小心地绕过拐角,生怕踏错一步就要跌下深渊。眼看她就要跑掉了——她已经奔到门前,这时门
又被风带上,她只好停下脚步去开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罗洛一把抓住她的衣领,另一只手攥住她外衣下摆,把她拽回走道上。
罗洛拖着她后退,她双手乱挥,脚跟拖在石路上。她故伎重施,双腿一软,但这次行不通了,反倒叫罗洛省了力气。他退到了角落。
罗洛一只脚踩在墙沿上,想把她拽上去。墙根凿了排水孔,她一只手死死抠住孔眼,接着抓住墙沿。罗洛对着她胳膊就是一脚,她松开了手。
她半个身体悬在墙外,脸朝地面,吓得失声尖叫。罗洛放开她的衣领,想抓住她两只脚腕往下推,但只抓住一边脚腕,另一只却够不着,只好作罢,把手高高抬起。她就快翻下去了,但双手还紧抓着墙沿不放。
罗洛于是抓着她一只胳膊;她松开了手,身子栽了下去,但最后一刻却抓住了罗洛的手腕,险些把他也带下去,好在她体力不支,手还是松开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