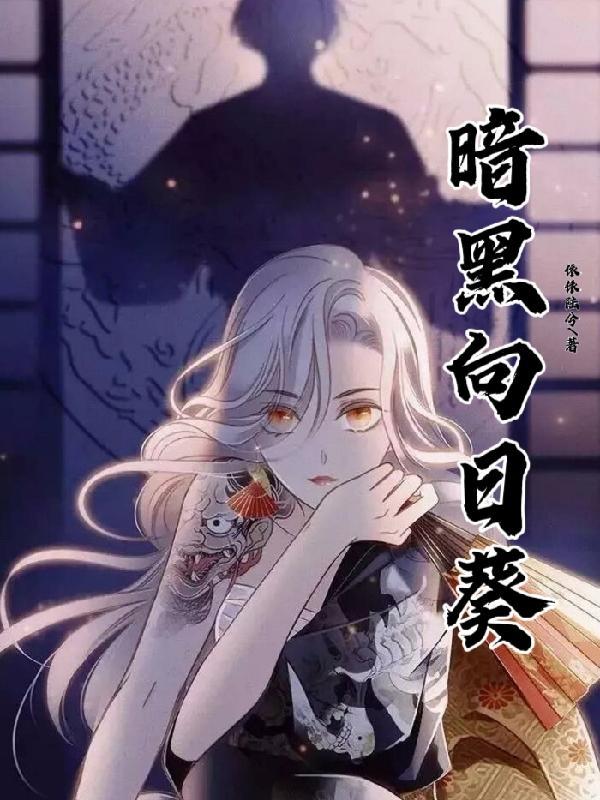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报错恩后我重生了 > 第152章(第1页)
第152章(第1页)
他用指腹在她手背处摩挲几下:“近日没来看你,是因为有些事情必须要尽快处理,朝中近来动荡,京中可能不太平,我会让人保护好这座小院,必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”
姜醉眠追问道: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跟将军府有关?”
听出她语气中的担忧之意,陆昭珩神色便有一瞬间的僵硬,可是怕被她看出来,他又很快面色如常。
每每提到将军府她总是异常紧张,赵棠虽然人不在这里,却还是能让她这般牵肠挂肚。
陆昭珩道:“有关。”
姜醉眠眉心紧紧蹙起来,她手中也用了点力气:“我也有事想跟你说。”
一边说着,姜醉眠另只手准备悄悄摸到枕头底下的那封信,可是在即将触碰到枕头的时候,她又有了片刻退缩。
“陆昭珩,”她道,“你也认识我父亲。”
“嗯,姜国公战功显赫,受万民爱戴。”
“可那都是过去,”姜醉眠眼底有些酸涩,“他私通辽人,背叛了大宴,最后连累了姜氏满门被抄斩。”
陆昭珩伸手轻轻抚上她脸颊,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她父亲的事,虽然她在强装镇定,可他听得出她话语中的悲恸和颤抖。
“等到眼下的动乱平息,我会命人重审当年案件,必不会让一个冤魂漂泊无依。”
他语气郑重,像在陈述,更像在宣誓。
姜醉眠忽然紧紧揪住了他胸口的衣襟,被月光映亮的双眸在急剧颤动:“你也相信我父亲是被冤枉的,对不对?仅凭着几封密信就给父亲定了罪,这难道是符合大宴律法的吗?这其中就没有什么可以操作的余地?那些信的来由真的有被认真核实过吗?如果私通辽人的另有其人怎么办?如果父亲一生清白都被那区区几封信毁掉了怎么办?如果我姜氏满门都是被小人故意构陷,那上百条人命就白白断送了怎么办?”
她越说越激动,激荡的内心难以平复,眼眶一阵阵热意涌上,长睫扑簌簌颤动几下,清泪便争相从眸中掉出来。
看见她神色痛苦近乎宣泄般的在哭,陆昭珩心口像是被把钝刀子在细细密密的磨,磨得他痛如刀绞。
“我知道,我都知道。”
他松了她的手,上前将她径直搂进了怀中,一手避开她腹部,轻轻环住她腰间,另一手在她发丝上轻轻柔柔的抚着,带着安慰意味,任凭她将眼泪尽数埋进了自己胸前。
“我从来不相信姜国公是会通辽叛国之人,他清廉正直,一心为国,只是当年案件判得草率,现在回想起来诸多漏洞,还需一一查清。”
他低头,在怀中人的发心上轻轻落下一吻,低声劝哄道:“等到案件查清,一切自会有定夺,不哭了好不好?不然明日眼睛会红肿得像兔子了。”
姜醉眠这几日一直在压抑着内心情绪,旁人不知她为何会如此针对赵筠,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只是想为父亲翻案而已。
知晓她身份的只有陆昭珩,在他面前她倒是可以不必辛苦伪装。
她抬起头来,泪眼朦胧地问:“那还要等到何时?何时才是重审案件的最好时机?”
陆昭珩在她后脑勺上揉了揉,定定说道:“快了。”
旁的,他却并没有多说。
那些事情太过危险,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,他不愿让她知晓,更不愿让她牵扯其中,所以回京之后便不敢来此看望她。
等到他将一切危险障碍扫除,再让她安安心心成为他的太子妃。
陆昭珩直到天蒙蒙亮起才离开,姜醉眠还在榻上沉沉睡着,脸颊上的泪痕已经被人小心翼翼的擦干,那只小奶兔也被放在了她怀中睡得安稳。
姜醉眠午时才起,两只眼睛确实红通通的,还有些肿,看起来昨夜像是不知道经历了什么。
那封信她最终没有给得出去,陆昭珩说还要再等等,可是要等到何时,他却没说。
又过了两日,姜醉眠去了趟太医院,她记得当日进宫面见皇后时听说过,今日是太医院给皇后请平安脉的日子。
皇后身边的掌事太监去太医院请人时,见着了姜醉眠,掌事太监长了个心思,记得皇后娘娘对这位女太医格外欣赏,便请了姜醉眠一同前去。
到了皇后宫中,皇上恰好也在。太医给皇后请完脉后,姜醉眠又给皇后诊了诊脉,并说出了皇后吹过风后便会经常头痛的毛病。
随后她为皇后手臂上施了几针,惹得皇上和皇后对她皆是赞叹连连。
皇上问她要什么赏赐时,姜醉眠却没有言语,反而颇为艰难的跪在了地上,垂着眼眸,模样清冷倔强。
皇上见她一个大肚子妇人如此这般,问道:“你可是有话要跟朕说?”
姜醉眠道:“民女只是有一事不明,想请皇上和皇后娘娘为民女指点一二。”
皇上须发已见白,脾气秉性也比年轻时候要温和许多,且已经生出了退位之心,所以现下最是仁慈爱民之时。
他道:“既然已入太医院,便也是我大宴臣子,有何事但说无妨。”
那封密信就静静躺在姜醉眠袖口中,她攥紧了指尖,犹豫不决。
早已经想过千遍万遍的说辞,到了此刻竟然有些哽在喉间。
皇后娘娘本就对她颇为喜爱,想命人将她搀扶起来:“地上凉,你身怀六甲,还是起来说话吧。”
姜醉眠谢了恩,却仍旧没有起身,她抬起头,黑眸清亮。
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,没人知道。
她只知道此时此刻对她而言就是最好的时机,再继续等下去,难道要等到赵筠彻底权倾朝野的那一天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