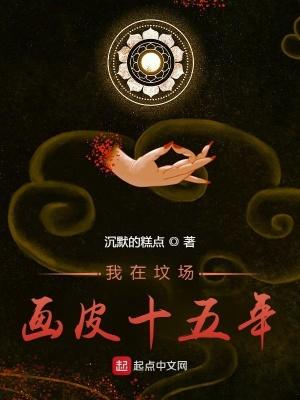UPU小说网>枕叔 绿药晋江文学城 > 038轻吻(第2页)
038轻吻(第2页)
到了雅间,封岌终于可以将脸上的面具摘了。今夜很暖,戴着面具有些闷。
菜肴皆已端上来,他未尝其他,先尝一尝寒酥给他赚回来的酒。三杯下肚,他才拿起筷子吃饭菜。
寒酥安静坐在一侧,并没有动筷。
她现在只想回府。
她来赴约,可不是为了莫名其妙陪封岌吃喝闲逛的,而是为了半月欢
毕竟他是在她那里误食。
当日沅娘给了寒酥好几种药,这种半月欢并非她所要的最烈的药。半月欢会在持续小半月里时不时勾起人的旖念,尤其见到异性时旖念更深急欲纾纵,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药效会一日强过一日。
她偷偷望一眼封岌,见他正大口吃着东西,不由心下好奇半月欢是对他没用吗如果对他没用,那他找她出来又要做什么
“吃些东西。”封岌道。
走了那么久,寒酥确实有一点饿。想着封岌坐在她左侧,她才摘了面纱,开始吃面前的一碗清粥。
才吃了一口,她才现这不是青菜素粥,里面竟有肉丝。她轻“呀”了一声,有一点茫然。
她在守孝,一直吃素。
封岌撕下来一只鸡腿放在寒酥面前的空碟里,道“我父亲去世的第二日,我便饮了酒。之后更是从未吃过素。难道是我对父亲不敬不孝”
“当然不是”寒酥赶忙说。
“孝不孝并不应该拘泥于形式。你父亲在天有灵看你日渐消瘦,不会觉得你孝顺,只会心疼。”封岌又夹了一大块小酥肉放在寒酥面前,“多吃些肉,你太瘦了。”
他又感慨了句“还有丁忧三年,简直是最愚蠢之事。”
他这不是随口感慨,而是想到了认识的几个人正是报效家国时,却因为丁忧不得不暂时离开仕途。
在他看来这是对自己生命的蹉跎,于朝廷来说也是憾事。
封岌又挑了些荤菜递送到寒酥面前。他刚将一个浇满油汁的红烧狮子头送过去,略沉吟,又把那块红烧狮子头拿回来,道“你吃素太久,暂时别吃太重油的吃食。”
寒酥望着面前堆成小山的菜肴有一点犯难。不得不承认,她确实有被封岌说服,而且这些肉食真的太香了
这一晚上,见他始终优哉游哉,实在不像受药物影响的样子。可是昨天晚上他又确实红了眼睛
封岌看着她的慌乱,沉默了片刻,道“寒酥,你看着我。”
这儿是酒楼里最好的上房,宽敞不说,其内家具和装扮也都精致不菲。
他沐浴过后草草擦身,健硕的上身残挂着一点水珠。水珠沿着他硬邦邦的胸膛缓慢往下坠,消于他腰侧的伤处。
寒酥现了,微惊之余指尖轻颤了一下,她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,随着她突然的动作,面上的面纱突然滑落。
“看我的身体。”封岌问“我身上有什么”
寒酥知道他腰间有伤,上次还帮他上过药。不过那伤口很浅,并不碍事。寒酥还以为那伤处早就痊愈了,此刻却见流了一点血。
微疼的伤口上被灼烫了一下,寒酥心尖跟着灼烫了一下。她怔怔望着封岌的眼睛,似乎又掉进了他深邃的眼底。
他朝寒酥迈出一步,几乎贴着寒酥。他抬手,宽大温暖的掌心撑在寒酥的后颈,迫使她抬起脸来。
封岌的视线落在寒酥脸上的面纱,沉声“你的亦是。”
寒酥仍旧立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。封岌将脸上的面具摘了随手一放,又脱下外袍。他语气随意地开口“不愿意和我同榻”
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。分明当初划伤自己时十分决然,分明这段时日从未后悔当日做法,分明别人关切时她也可以揭开面纱给别人看,分明毫不在意别人的惋惜或奚落。
直到跟着封岌迈进房中,寒酥才彻底明白他原就没打算带她回府,而是要宿在外面。
寒酥略湿的目光徨徨落在封岌的胸膛。他赤着的健硕胸膛上,遍布许多旧伤留下的疤痕。那些疤痕印在他的胸膛上,不显狰狞,是另一种傲然雄伟的姿态。
“不是”寒酥立刻去夹了一小块小酥肉放进口中。
寒酥吃了不多便放下筷子,重新戴上面纱,安静坐在一旁等封岌吃。她看着封岌也吃完了,却没有要走的意思,实在忍不住开口问“我们什么时候回去”
封岌抬眼,声音沉“不吃是等我喂你”
不能吧,他哪里有那般神通广大。
她脸上的伤口刚结痂,划伤周围又肿起来,正是最丑的时候。寒酥有一点难堪,心中一慌,匆忙去戴面纱,因为太焦急,第一次没能将面纱挂上,第二次才戴好。
寒酥摇头,默默又吃了一小块小酥肉。
寒酥突然落下泪来,泪水将面纱黏湿。
“将军流血了。”寒酥道。
她现在明显已经不再完全信他的话了。